“要是我死了,你就吃了我,当作我在人世间做的最后的施舍。”

这是电影《雪豹》中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台词。仿佛阴郁的预言,去年五月,这部作品的导演万玛才旦猝然离世。这位从文学系转行的电影人有着很多头衔:“藏地新浪潮”电影的领军人物、中国百年影史藏族母语电影的开创者......而用万玛才旦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写小说、拍电影,讲故事的人。
最近,《雪豹》走入院线公映,万玛才旦的遗作小说集《松木的清香》和翻译作品《如意故事集》也即将出版。本期「乒乓台」,于是和竞菲从《雪豹》观后感谈起,与我们共同回顾万玛才旦留下的那些未完待续的故事。
正如阿乙在《如意故事集》的推荐语里所说:“故事就像星星。星星可能已损毁,但它发出的光还在到达我们的路途上。”或许,万玛才旦所做的一直是在不同的世界观之间转译的工作。在他的文字和镜头中,藏地终于得以挣脱被景观化的猎奇书写,回到在地者那些真实的生活细节——男与女、人与豹、种羊与iPhone手机和谐共处;跳出二元对立的僵化框架,万玛才旦寻找的,是现代人共同的母题。
【本局单打选手】


【本期书影】

【本局精彩回合】
02:28 万玛才旦电影遗作《雪豹》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04:36 传统与现代的对峙是万玛才旦创作中一贯的主题
07:26 作为译者的万玛才旦和他的藏地版“一千零一夜”
12:36 《我是一只种羊》《老狗》:万玛才旦作品中的动物视角
22:20 中国电影史中的藏地题材电影
32:22 “万玛才旦的语言,是对当代写作过于修饰性的一种反拨”
39:09 藏地“新浪潮”的浪还能更大一点吗?
42:34 万玛才旦对现代性的批评是在二元对立的框架之外的
51:54 为什么有人评价万玛才旦是中国的阿巴斯?
58:12 推荐环节:《樱桃的滋味》&《雪豹,或最后的诗篇》
【节目中提到的人名和作品】
·人名
金巴(1985-):藏族新生代电影演员、诗人,进修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
厄休拉·勒古恩(1929-2018):美国科幻、奇幻与女性主义与青少年儿童文学作家。
德格才让(不详): 藏族,来自安多藏区 。先后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录音系、西北民族大学藏语言文学系。 独立电影人、电影录音师、作曲、编导。
江洋才让(1970-):男,藏族。青海作协理事。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作家班。
久美成列(1997-):中国内地导演、编剧,2021年,执导悬疑警匪电影《一个和四个》,万玛才旦之子。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1940-2016):生于德黑兰,是伊朗革命后最有影响力和最引起争论的电影导演、编剧和制作人之一,也是过去20年国际上最著名的伊朗导演之一。
陈丹青(1953-):生于上海,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家、作家、文艺评论家。
田壮壮(1952-):中国著名男导演。北京人,是著名电影演员于蓝和田方的儿子。1978年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系,与陈凯歌、张艺谋等人是同学,是第五代导演之一。
吴天明(1939-2014):自学成才的导演。1979年与滕文骥联合执导《生活的颤音》崛起影坛,独立执导《没有航标的河流》而受人注目。《人生》是他的代表作,《老井》、《变脸》成就了他艺术创作的高峰。
顾长卫(1957-):中国内地电影导演、摄影师。
侯孝贤(1947-):台湾电影导演。父亲原本为当地的教育科长,1948年全家移民到台湾,属外省籍客家人。侯孝贤喜爱使用长镜头、空镜头与固定镜位,让人物直接在镜头中说故事,是他电影的一大特色。
杨庆祥(1980-):原籍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现居北京。诗人、批评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松太加(1974-):生于安多藏区,著名藏族导演、电影摄影师,编剧。曾以美术和摄影身份参与拍摄《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老狗》等获奖影片。
东主才朗(1983-):青海贵德人,制片管理、演员。
小津安二郎(1903-1963):生于东京都深川。早期他广泛的拍摄各类影片,其中又以青春喜剧类居多。战后则主力于以一般庶民日常生活为主的小市民电影,尤其以《晚春》、《东京物语》为他一生中的代表作。
·书籍
《乌金的牙齿》《故事只讲了一半》《松木的清香》《如意故事集》万玛才旦
《雪豹,或最后的诗篇》江洋才让
·影视
《静静的嘛呢石》《气球》《老狗》《寻找智美更登》《塔洛》万玛才旦
《旺扎的雨靴》拉华加
《樱桃的滋味》《如沐爱河》《合法副本》[伊]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
《盗马贼》田壮壮
《冈仁波齐》《皮绳上的魂》张杨
《阿拉姜色》松太加
《独生子》[日]小津安二郎
你可以在以下收听平台找到【乒乓台】:

喜马拉雅:

网易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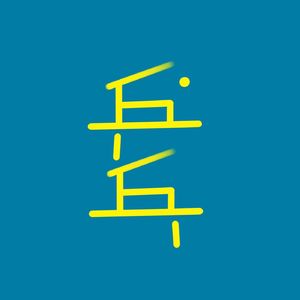

 949
949 35
35











万玛才旦有点像黑泽明,不是电影本身,而是他们都用另一个文化体系中的工具做出了非常本土的作品,又让这工具的本来使用者转过头来学习和崇拜。同时也像黑泽明一样,培养了一群电影工业的从业者。但是万玛才旦是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
还记得半夜读那篇种羊忍不住笑,我老婆问我你有什么毛病了?
每个人留下的东西,都是恰如其分的,不是过多的或过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