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聊一个,被反复翻炒的焦虑话题:在人工智能浪潮席卷而来的时代,我们文科生究竟该何去何从?
前段时间网络上充斥着"哈佛大学取消30多门文科课程"的爆炸性标题,评论区里随处可见"文科生末日论"。但真相往往藏在细节里。当我们打开哈佛官网,会发现这所拥有3700多门课程的学术殿堂,仅研究中文语言的课程就有30门,《元代白话碑研究》《藏语口述传统》这样的课程依然在列。这就像有人说"北京某商场取消停车优惠券"等于"北京商业要崩溃"一样荒谬——某些自媒体用局部调整制造全局恐慌的伎俩,值得我们警惕。
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分享一个真实案例。有一位研究《文献通考》的学者在破译元代文书时,AI成为了她的研究加速器。当遇到蒙古语直译的特殊语法时,AI能瞬间调取历代译本的比对分析;需要检索元代经济制度研究时,AI给出的书单让元史专家都点头认可。但最关键的是,当AI整理出38篇相关论文后,真正判断哪些文献具有突破性价值,哪些观点需要商榷批判的,依然是学者本人的学术眼光。
这让我想起古登堡印刷术刚出现时,教会担心《圣经》的批量印制会摧毁神学权威。但历史告诉我们,活字印刷反而催生了宗教改革,让思想传播得更远。今天的AI之于文科,恰如当年的印刷机——它正在重塑知识生产的形态,但永远替代不了人类独有的三种能力:
第一是价值判断的能力。当AI能生成100种《哈姆雷特》的现代改编版本时,决定哪个版本最能触动当代观众心灵的,依然是具备人文素养的戏剧导演。
第二是跨文明对话的能力。有一位研究敦煌文书的学者说,AI能精准识别出某幅壁画中的犍陀罗艺术元素,但要理解这些元素如何沿着丝绸之路完成文化转译,需要的仍然是人类学者的文明洞察。
第三是创造新范式的能力。2015年,有一位历史系学生用GIS技术重现了北宋汴京的城市生态,这个将数字人文引入传统史学的创举,靠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打破学科壁垒的想象力。
现在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顶尖科技公司的用户体验团队里,越来越多哲学、心理学背景的人才开始主导AI伦理设计;在文化遗产数字化领域,艺术史学者正在训练能识别壁画病害程度的AI模型。这些都在告诉我们,文科生的真正竞争力,在于将人类数千年的文明积淀转化为AI时代的"数据养料"。
当然,这也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有一位社会学教授,五十岁时开始自学Python 编程语言,他说:"我不是要成为程序员,而是要让机器理解什么是'社会资本'。"这种持续进化的勇气,或许才是应对变革的关键。
最后,我想用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座右铭与各位共勉:"不要问机器能做什么,要问人类该做什么。"当AI能写出工整的十四行诗,我们更要写出震颤灵魂的自由诗;当AI能归纳历史规律,我们更要追问被算法忽视的边缘叙事。文科生的使命,从来不是重复已知,而是照亮机器永远无法抵达的人文星空。
好的,谢谢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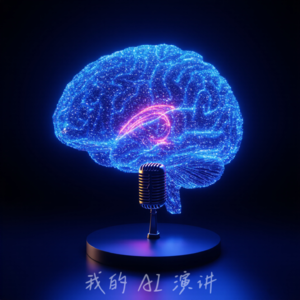


 0
0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