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凹凸镜DOC:许多人都是通过先看您的小说、影评,然后再看到您的电影,您如何看待这几种表达形式的优缺点?
徐浩峰:我上大学的时候受的是一个完整的训练,一周要在电影院里看两部电影,看完电影先跟同学讨论再和老师讨论。我上学的时代,我们的带班老师是郑洞天老师和江世雄老师,郑洞天老师当时给两个电影专业杂志写影评,所以从欣赏电影、分析电影到电影创作都是在同一个系统里的。
刚毕业时,原有的电影厂体系在转型改组,再没有别人直接请你当导演的运作制度,这种制度在我们这代一下就没了。所以作为导演系的毕业生,你得先练出一个本事,比较聪明的同学就先练编剧的本事,拿自己创作的剧本来争取导演的机会,要不然就先练拍电视剧或者拍短片拍记录片的本领,等于比前一代人要多练一个手艺才能当电影导演。
我是先写影评,因为我那几年还没开始练剧本,当然也得写东西,所以我是属于练影评的那一类。
社社:您的影评新书《光幻中的论语——十七年电影的导演逻辑》,有一篇我特别喜欢,“《小兵张嘎》和塔尔可夫斯基”这篇。您这种结构方式和拆解理论的视角非常有意思,您怎么认同这本书在您整个创作图谱中的价值呢?
徐浩峰:以前做影评不能泛泛的谈自己的个人感想,以前写影评要有责任心,一篇影评一定要有五六个知识点,而且这些知识点还是你新挖掘出来的,这样才对得起读者,这是以前的影评标准。我年轻的时候做影评其实还是把从书本上看到的知识,或者是圈内的知识进行组接,把这些知识组接好之后再评一个大众都看到的电影。
现在做影评其实按照以前来说是犯忌的,以前影评不能光谈个人感受,个人感受是不准的,有局限性的,但是现在故意要犯这个忌。我把自己的一些生活经历,等于是没有文字记录的,但是,是我经过的一些事,我把它作为我的论据了。
凹凸镜DOC:我分享一个故事:在某一年的中国独立影像展举办期间,有些学者发表了一些对独立电影的评论,部分导演并不认同学者的观点,觉得,你们连拍都不会拍,你们写的影评能有什么?导演们发起来一个“南京宣言”, 用以直接表达对批评界的不满。您觉得影评和电影创作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
徐浩峰:国内最早的影评体系其实是学前苏联的评论方法,比较接近文学评论,是很完整的,有体系的。它其实是个论文,但它写得又易懂一些,不像论文似的要有那么多的注释。
80年代之后,巴赞、特吕弗、戈尔达的影评对我的老师那一代人的影响非常大,他们撰写的影评风格变为,一个影评得有五个知识点之外,还必须要把影评文章化,影评要有文学性,这等于是法国范。
以前的苏式影评是文学评论式的议论文,法式影评它本身是一篇漂亮的文章,追求文章化,所以这是我老师那一代。
凹凸镜DOC:您怎么看文学和电影的关系呢?
徐浩峰:首先,电影剧本和小说有很大的差距,比如,19世纪的小说,它建立了很完整的人物,这是19世纪的巨大的成果。这其实也是一个导演的思维方法,一个编剧的思维方法。但一个常规的电影两个小时,你的时间不够,因为你拿一个小说去塑造人物,完成这个事件要有很多的层次,这样才能建立起来,但是电视剧本无法有那么多的层次。所以电影剧本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结构的方法,我没办法直接写人物和时间,但是我对它进行分切和拼装,构成了一个电影剧本,这就是小说和剧本大致的不同。
凹凸镜DOC:文学作品改编成影像化的时候,您会有怎样的具体处理?
徐浩峰:你如果用文学,必须要用很多的层次,因为文学是一个字一个字拼出来的,文学要感人不见得总体字数很多,可能我只有40个字触动你了,但这40个字描述的层次非常多,在这40个字里你感觉到一次次海浪般的冲击,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而电影它其实做不了这么多层次,所以有时候需要我拿一个镜头,把两页小说的内容变成两秒、三秒,这是一个叙述节奏上巨大的变化。
社社:您如何在作家和电影导演这两个身份之间来回切换呢?
徐浩峰:我最早拿小说给电影做热身,因为电影剧本要求的结构太严密,写电影剧本修改的时间太长,你得在反复改很多次中去找,怎么才能表达出来的分寸,否则将来一拍电影,你觉得自己感情充沛,但是拍了一堆废戏,剪的时候还是得高度精简化的舍弃去剪。与其这样,在剧本的时候就去练,写剧本的时候已经有了淘汰和筛选的过程,在剪辑台上就省事。
小说其实是要找你的主题和构思,一开始的时候,你想的主题一定是比较肤浅的,通过各种方式写一个事,把这个事写出来了。
社社:《大日坛城》的主题,您一开始想的是什么呢?
徐浩峰:我们不管他叫主题,它其实是一个构思。我们不拿电影这个形式去说思想,而是设计出一个思想性的情节。等于是我们也谈哲学,但你说徐浩峰老师你的哲学是什么?我说不出来,因为我们是情节化的哲学,所以《大日坛城》的基本构思一开始吸引我的是一场一场的棋战。我喜欢围棋,曾给《围棋天地》写过短篇文章,给《解放军报》写过评围棋的长文。
凹凸镜DOC:刚才您提到一点,您想做导演先从文学或者编剧来练手,但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影像的平民化,很多年轻人可能上来没毕业就可以当导演了,不像您那时候有一个过程。但我自己反思,可能有一种对影像的敬畏消失了,太易得到了反而不珍惜。您做第一部作品的时候是不是很忐忑?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徐浩峰:我们那个时代拍影像要付出很大代价,因为那时候的拍摄介质还是胶片,等于是化学时代的电影。第一次当导演其实都会紧张,这个紧张是总怕自己把东西拍漏,会有那个焦虑,会恐慌,总担心自己有没有拍够。因为那时候导演经验不足,还未能建立起整体的概念,导演经验丰富之后就觉得就拍到这其实就够了,因为还有别的戏别的镜头,一拼效果就很好。
第一次拍电影往往会陷入一个思维的误区,就是把一个镜头当作整个电影来拍,你就觉得一个镜头得表达我所有美学,给自己搞的压力也很大。
凹凸镜DOC:这些年“武侠影片热”似乎在慢慢消退,当然会有一些变种,一些片子虽然不是武侠题材,但还是有一些武侠元素,您怎样看这样的现象呢?
徐浩峰:武打片的鼎盛时期,其实都是以中国人的人文作为依托的。70年代的武打片鼎盛时期都是写一个老式家庭的故事,黄飞鸿和他的父亲,黄飞鸿开药铺的街里街坊,人情世故,一条街上有两个武馆,两个武馆之间(的故事),他等于有民风作为故事的一个依托。后来随着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大量的在现实生活里消逝,年轻人不喜欢看这种片子,因为我在生活里没有同感,成龙是典型的由武打片变成动作片的代表人物。
那时候的电影完全脱离民风了,会写一个侦探小说里的侦探,会写一个警察,但是动作片中又有武术的元素。后来徐克、程小东发明了一套新的视觉观念,让以明朝服饰为主的一套片子开始流行。但是后来因为大量的复制而不注重故事,都是即兴的编戏,突然一下在东南亚、大陆和香港本土失去观众群了,这跟他们视觉设计高度精良化、剧本粗糙化有直接的关系。
凹凸镜DOC:能聊下您的新书《光幻中的论语——十七年电影的导演逻辑》撰写的背景和过程吗?您为什么会对十七年电影感兴趣?
徐浩峰:那些都是我童年时期看的电影,那时候写的人物的风貌,接人待物的方式,你看了就会明白中国为什么被称为礼仪之邦,即便在民国,大家都普遍西化,传统礼仪高度简化,这些人物,你不看他们的故事,光看他们说话和动作,你会觉得非常好看,他就已经是礼仪之邦里最简化的礼仪了,但是那种彬彬有礼的东西非常让你感动。其实最早就是想追究孙道临、于蓝这些演员他们怎么说话,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说话。
凹凸镜DOC:研究十七年电影,您觉得对当下的电影是否有一些启发呢?
徐浩峰:导演创作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拿这个行为反应社会,这个行为不是说你对抗一个剧烈的外部世界,而是,比如说这个人在家里他打不打孩子,这个人和朋友发生冲突之后,朋友之间最激烈的方式是什么?用个人小家的行为的变异来反映社会的变异,这是导演构思的一个方法。
所以十七年电影就是去研究这个行为跟社会进程的关系,它算是一个样板。
你看到那种彬彬有礼的行为,但是他又发生了革命。现在的人可能对不自知的一些行为方式觉得理所当然,但是以导演的眼光看就觉得太奇怪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仪态和举动,背后一定影射着什么东西。所以社会信息是非常具体的,是直接落实在人的言谈举止上的。
凹凸镜DOC:未来会不会想尝试除了剧情片以外的方式,用纪录片、漫画或者其他形式继续阐述“武林”呢?
徐浩峰:不会,因为我跟武术界的默契是,我不介入武术界的事,之前有过多部武术纪录片请我做顾问、受采访对象,都婉拒了,这是电视界普遍知道的,所以现在也没人找我了。动漫,是我不了解的领域,有过动漫想请我做武打动作设计,也婉拒了,我这年纪,精力有限了,为避免给观众添乱,就不做不熟悉的事了,能把我熟悉的事做得再有提升,更对得起观众吧。
本期时间线:
00:50 欣赏电影、分析电影到电影创作都是同一个系统里的,我是属于练影评一类
09:18小说成就人物、讲述事件有很强的层次性,但电影剧本主要对它进行分切和拼装
12:35 我们不拿电影这个形式去说思想,而是设计出思想性的情节,讲情节化的哲学
15:55第一次拍摄没有整体的概念感,就想把一个镜头当做整个电影来拍,什么都是重要的
23:45 行为反应社会是导演创作里很重要的概念,用小家的行为变异反映社会变异,看到内化的东西很重要
联系我们:
微博@社社不是唯一的水果
公众号|社交车间
邮箱|875353129@qq.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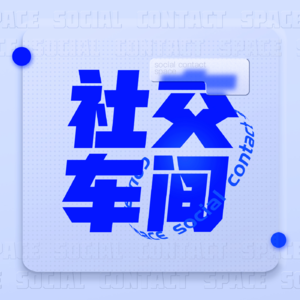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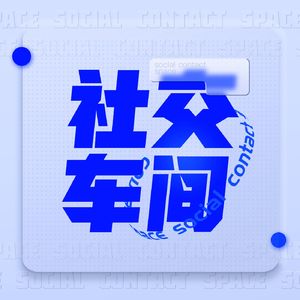

 1229
1229 22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