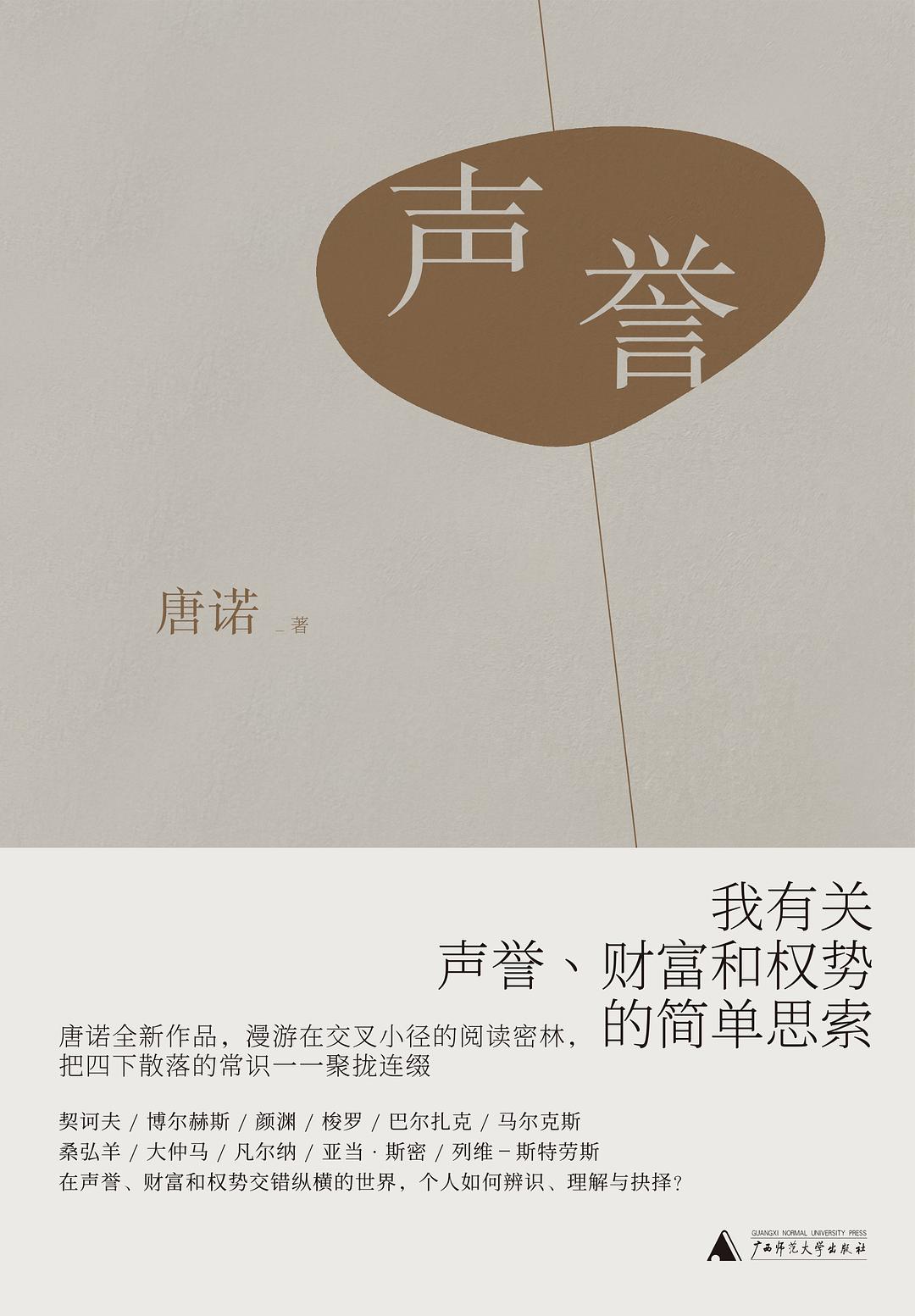
【导读】
积攒了一年多的读书会库存清空了,开始了和听友同步阅读的路程。以后的更新频率可能没法固定,也许很快,也许很慢;于是,我们想了一个新的分享方式:从「阅」到「读」。
上期然少分享了茨维塔耶娃的诗歌,接力棒来到了我这里。
今天分享的是我非常喜爱的作家唐诺的一本书-《声誉》,副标题是「我有关声誉、财富和权势的简单思索」,选择阅读的部分是靠近全书结尾的一个小节,因为直接与读者、书籍相关。由于脱离了全书的脉络,有些观点难免会稍显突兀、缺少铺陈,甚至可能会有人感到冒犯。无论如何,要是因此能让一两位听友提起兴趣去阅读这本书,这期节目就算是功德圆满了。
【原文】
从读者到消费者
编辑有两种屡屡不相容如双面间谍的忠诚,他得同时服侍财富之神和声誉之神;读者一样也两种身份集于一身,就财富世界的供需位置他是顾客,一个高出于书(商品)的身份,而就声誉世界的古老规矩他则是学徒,一个由最底处开始的谦卑身份——人在(实体)书店的经常性肢体姿态,巧合但不无巧妙的大致呼应着他的此一双重身份,他总是俯视、随手翻拣摊平热卖的书,也仰起头搜寻,伸手向书架上层的某一本书。
本来是这样,但整个大世界继续向财富面倾斜,必然的,也人性的,读者也逐渐只留下顾客这个较舒服的身份,书店是所谓的一般零售业商家而不是某个“殿堂”,实际交易过程跟着如此变异。
实话实说,我自己最在意的是书籍世界的此一人心变异,几乎是痛恨了——这个讨厌的东西叫“消费者意识”,让人放纵自己、误以为自己可指指戳戳胡言乱语、还以为所有人时时处处计算侵犯你权益。当然,谁都晓得这本来有正当性而且必要,但很快就全面越界了滥用了,还迅速接上集体暴力(通过网路再方便不过),也许糟糕的正因为那一点正当性必要性,为人的自私和愚昧披上社会正义的外衣,成为某种正当的愚蠢和公义的自私(但有这种怪东西吗?)。如今,这在各个较纯粹商业交易行为的领域里都是讨厌的,遑论书籍世界,而且早有各自的固定称谓,可见行之有年及其普遍性,比方在学校称之为“怪兽家长”,在一般商家则叫“奥客”云云。这十几年时间,我几乎一天不缺席地在咖啡馆工作且冷眼旁观,“累积飞行时数”约三万个小时,而且无利益、没兴趣、不参与,正是汉娜·阿伦特所说最宜于看清事实真相的位置,我以为我有资格提出这样一个人类学式的田野结论:我亲眼所见从发生到结局的两造纠纷,十次有九次半是顾客的问题,顾客无理找碴,或者因为自己没搞清楚,或者只因为心情不好出门前和家人吵了一架,或者是他本来就以为自己可以这样、他就是这种人——
咖啡馆川流不居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是小女生,年纪二十上下,多半是工读学生或才毕业,时薪一百元出头,她们同年龄同班的朋友此刻可能正舒舒服服宅在家里连自己杯子都不收不洗,很多人家里有这样的女儿。说说看,欺负她们究竟有哪一点社会公义可言?带种的话以相同方式、相同话语对自己女儿也来一遍如何?
每天早晨,我花一百五十元(从七年前的一百元合理地缓步调升),得到一份颇丰盛的早午餐,两杯咖啡(可续杯一次,但常常不止),一个书写位置,五小时左右的工作时间,还有她们节制的、沉默的善意和侍候。我的家人若肯这样,我乐意每天付五百元甚至更多并感动莫名(如今所有当人家父母的多会这样);我也跟一些对我工作状态好奇的朋友解释计算过,把这想成是每个月四千五百元租用一个办公室写字楼,还附管家和厨师(且食材由她办理并全额支付),听过的人都很惊奇原来如此划算——这一百五十元,我自始至终不认为还该多换取到什么,我更不相信、打死都不信,只因为我付了这一百五十元,就让我摇身成为事事正确、永远正确、从心所欲连圣哲和基督教的神都做不到的人。是非善恶尽管时时处处辨识不易,但自有其严谨不夺的判准,权势与财富,如果强权如苏格拉底所说不该就是正义,使用金钱也一样必定不就等于正义,还有比这个更明显的道理吗?
尽管绝对平等会破坏不少东西,平等的思维得有其边界,但人是平等的,我以为这是人跟人各种复杂多重关系的唯一根基,唯一可能、或者说绝不容许退缩取消的最终底线。然而,作为一个读者的时候,我会“明智”地让自己(暂时)站在一个稍低的位置,当然不是毁弃此一原则,更不可能是对还收你钱的书店、出版社,其实也不尽然是针对书写者本人(如中国人讲君子有三畏之一的“畏圣人之言”,不是敬畏说话的人,而是他讲出来的话语和道理),是因著书里那些高远的、本来就比你此刻所在高而远的好东西。我自己从不喜欢(事实上不免感觉有点恶心)那种“在××面前,人必须学会曲膝低头”的说法,不管这××填的是真理、正义、是非善恶云云;我宁可说这其实是自然的或说物理性的,不是曲膝而是抬起头,你仍是直挺挺站着的,你看一棵大树、一座山、一天星辰,不就自自然然是这个姿势吗?
把粗糙的平等用在这里,不是道德错误,只是很不聪明而已,如同平视的目光会错失所有高处的东西;若进一步用消费者自以为居高临下的视角,那就是愚蠢了,这样的人即便站到喜马拉雅山前,能看到的也就是脚边的乱石野草而已——这里我说愚蠢不是骂人的话,而是一个中性、平实、求其精确的用词。这样做真的非常非常愚蠢。
二〇一五,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在戛纳得奖并首次在中国大陆院线上片,首映时,我因自己新书《眼前》的出版事宜人在北京,评论一片叫好,但我其实很担心票房不当地太好,进来太多错误的观众——电影远比文学深植财富世界,好莱坞侍候观众的能耐登峰造极,以至于电影早已如昆德拉所说封闭了其他可能,电影观众的消费者身份极单一排他。台湾我不担心,相关话题吵了已二十年,大致上人们已知道怎么看(以及绝不看)侯孝贤的电影,上帝归上帝恺撒归恺撒,还学会记得带个枕头进场因为不免睡着;中国大陆的影视热潮才起,却已是全球最大单一市场,这一切来得又快又急又浅,像地理学所说的荒溪型之河,都不断听见金钱的各种撞击声音了,绝大多数人们因此只(来得及)看过“一种”电影,乃至于认定电影只此一种,打从卢米埃兄弟开始就是这样。一旦不符合如此窄迫的观影习惯观影预期,人很容易觉得被骗了被占便宜,很容易被莫名激怒,很正当但愚蠢的愤怒,以及所有跟着而来很正当但品质愚蠢的发言。
我总会不断想起耶稣赴死前在客西马尼园里那番“分别为圣”的谈话(可想而知,好莱坞大片《达·芬奇密码》绝不会留意极可能正是耶稣一生最深沉触动的这番话语;服侍消费者买书人的丹·布朗没这脑子,也没这个习惯)。是啊,能否把这分开来,相互憎恶也没关系,只是让那些对的以及假装的观众好好看一部电影?——我当然晓得这不可能,愈来愈不可能了;而且电影比文学更不可能,电影的规格、成本太大太昂贵(可想成和书籍之比是三亿对三十万),它更难脱离财富世界的掌控,这是电影作为一种创作形式、思索形式较脆弱、少掉太多自由的地方。
大导演们如黑泽明最赞美乃至不胜歆羡侯孝贤的正是自由,久违了的、原来还能这么拍电影的一点点自由(从文学书写来看的确不太多),这多少是靠着侯孝贤本人的“鲁莽”和不在意才堪堪存留——不在意什么?侯孝贤确确实实是我一生少见最不在意名利的人之一,生活也一直过得如此简单,这当然是同一件事。
仔细回想,我自己这大半生也不乏进入电视电影世界工作的各种机会,但我一秒钟也没动过这念头,一直到今天,我仍觉得自己是明智的;还有福克纳这个怪人,他一生不断缺钱,解决的办法是心不甘情不愿去一趟当时已如金粉世界的好莱坞,负责编写修改当时的冷硬侦探电影剧本(汉密特、钱德勒等),但福克纳非常厉害,他赚到设定的有限金额,便掉头回到自己的南方小说世界,绝不多停留一分钟,我不晓得还有谁能做到这样。
所有作品都得接受检视批评,这是声誉最不容情到届临残酷之处——还不是只一小段时日、一种思潮或意识形态判准。我们说真正的声誉是在本人死后很久才堪堪完成,这意味着作品得经历各个不同时代,各种不同现实情境,通过各种思维和视角,所以,一个书写者创作者顶好先相信并做好心理准备,自己所犯的每一处可能错误,想错的、记错的、写错的包括笔误、心存诡计侥幸的、情感情绪失控的,乃至于只是校对印刷失误,每一个都躲不掉,都会在漫长时间大河中被某人看出来。除非是那些只配被遗忘的、消费物件也似的、所以也就无所谓的作品。
但不是这种消费者意见,这种“只因为我买了一张电影票”的批评方式、这种不爽——这真的有点悲哀,就因为一张电影票?能不能就退钱给你呢?
一直到今天,日本的饭店旅馆仍可分为两种,尽管另一种已渐渐稀少在财富世界如花凋零——我要讲的是某些通常一泊二食的传统和式旅馆。和后来的饭店营运方式不同,这种旅馆不是以设法满足顾客的一切可能需求为原则,而是倒过来,是我们拿出来我们认为最适合的、能力可及最好的东西和安排,你选择这个旅馆,代表你接受我们这样的款待方式,也许不同于甚至冒犯了你的某个习惯,但要不要安心下来、沉静下来好好体味我们为你认真准备的这一切呢?我们在百年来接待一个一个客人的时间里习得并不断调整的这一切?京都著名的俵屋旅馆,甚至会婉言提醒你不必住宿超过三天,三天是我们完整的一个接待循环、一趟旅程,超过三天就是又重复了,你不划算,我们也不心安。
这里面,隐藏着一个措词温和但不屈不让的专业思维,包括着这几句没说出口的话——有更多的好东西不在你既有的习惯里,远远超过了你已知的和已习惯的。



 202
202 1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