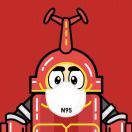新疆的行程结束后,两个月的时间,我几乎还在路上。三次返回新疆,两次穿越青甘,从陕北到银川,拍摄路遥、史铁生、张贤亮的文学现场,还跟踪了一只地质队和它年轻的项目经理。一个困扰着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些人可以把工作和生活本身当成是意义,我们大多数人都只愿意把意义寄托在别处?直到巴黎,我大概得到了一个早就应该获得的答案。如果人们长期按照自己的观点指导自己的生活,那生活本身就是有意义的。我们对于工作本身抱着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所以我们总是在生活的真实现场焦虑,然后幻想别处的生活。
更多关于“文学的现场”和“作家的故乡”,欢迎大家订阅我的星球。




 3787
3787 25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