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从照护到安宁疗护:有关爱与生命尊严的人生必修课》音频课。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系的教师刘谦,也同时是一名安宁疗护的志愿者,在这个单元里我将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我的死亡我能做主吗”这一话题。第一节我们就来聊一聊我的死亡,我可以做主的情况。
“我的死亡我做主”,其实是说我怎么样去管理临终的生命质量和生命尊严,生命的尊严是什么?生命的尊严大概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有能力去实现自己的一个意义系统,这是生命的尊严,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可能在一些情况下,也许人们宁可抛弃他的肉体之身。
当他没有意义系统可以附着的时候,他可能会做这样的选择,所以在临终阶段非常重要的是去整合非常破碎的意义系统,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生活的世界跟以前完全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在面对这样的生活境遇的时候,再去理解我曾经的意义系统?要么坚持曾经的意义系统,要么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做了一个处理,让这样的意义系统有了一个转换,使得我能够对我现在支离破碎的生活、羸弱不堪的身体,能有一个它之所以能够存在、还要存在和继续(存在)的原因或者是解释。
收听要点:
1. 我们为什么要讨论“我的死亡我做主”?
2. 如何“活出生命的意义”?
3.从“我的死亡我做主”倒推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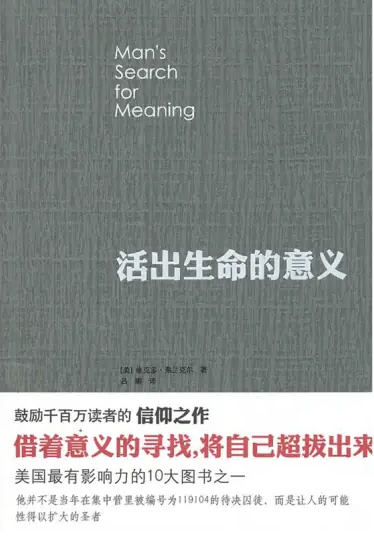
《活出生命的意义》
欢迎转发下面海报
共同走进这堂人生必修课




 18
18 0
0